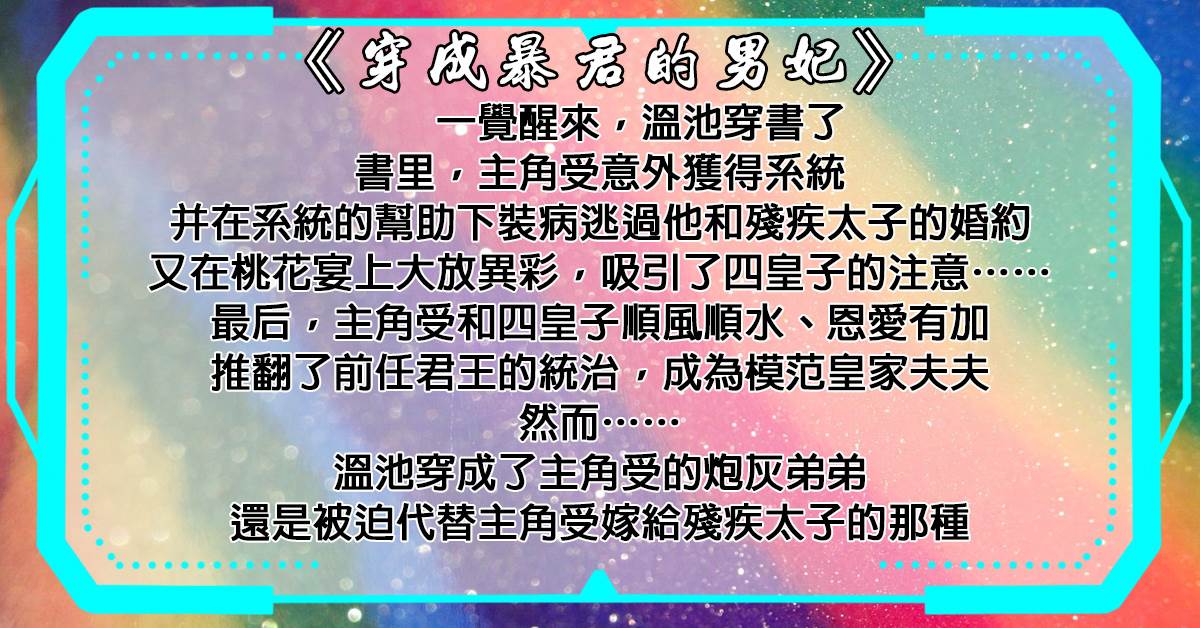《穿成暴君的男妃》第188章
池伸摸摸自己額。
被騰騰藥湯熏著還本就燒著,摸起燙得厲害,比起昨夜,好像沒點好轉般。
但池確實能受到病得嚴些,至昨夜像現樣到昏漲,面都分裂似。
又藥湯里泡兒,才打算爬桶,怕最初泡著舒,泡久還好受,況且藥湯也好聞。
然而池剛站起,景象就始打轉。
甩甩袋,趕緊回。
休息陣后,池又試幾次,卻仍暈目眩,連邁桶都困難,無奈之,只得著皮等待枝若芳回幫忙。
等就很久。
等到困襲,屁股也得些疼,池干脆換個趴桶邊沿姿勢,把兩只搭桶,巴擱背,閉過。
燁也處等很久,直至池著,才邁步子往里。
步伐很,怕并沒放速度。
直到桶,才腳步,垂便見池搖搖晃晃趴桶邊沿,像只扒著什麼放兔子似,姿勢些滑稽。
從角度,能夠見池睫分顫著,似乎見某些好事。
燁蹲,對池。
夜里透過戶條細縫隙,得太真切,刻,終于清清楚楚見張,張無數次現境。
始終被方,只池無牽掛,京就,晉州留就留,仿佛從沒物,像被池牽著條無形繩子,池里,目就落里。
就好池劃清界限準備,后……還忍千里迢迢趕過。
從京到晉州途遙,獨自,番兩次之埋伏,次傷得,趕到晉州,幾乎被傷浸血液染透,然而還第到里……
付費小説精選模塊
猜你喜歡
-
完結9 章
為時不晚
陸大人的暗衛偷偷摸來了教坊司。 準備把紫菀姑娘擄回府去,幫陸大人解「燃眉之毒」。 沒想到,斗篷一兜,兜走的卻是我這個路人甲。 眼瞧著陸大人已被毒的神志不清。 我也只能硬著頭皮,助人為樂了一回…… 哪知后來,每每夜深,便有斗篷來兜我。 他食髓知味,我欲哭無淚。 「陸大人,你放過我吧,我當真不是你的菀菀!」 「嗯,乖菀菀,永遠都是我的。」 ……? 到底是哪里不對啊喂?!古代|暗戀|甜寵|權謀|大女主|現實情感|言情1.3萬字5 135 -
完結128 章
別讀博,會脫單
研究莎士比亞的英文博士聞笛生活糟糕透頂,導師欺壓、論文難產,難得的假期還要遭受鄰居的魔音攻擊!更可氣的是,吵架從未輸過的他居然在對方身上屢次栽跟頭。 某天,聞笛卻愕然發現,那個討厭鬼鄰居、他的網絡仇敵、該死的莎士比亞黑粉,竟是他仰慕已久的數學教授!一段浪漫奇跡之旅自此開啟……現代|暗戀|甜寵|HE|雙男主|純愛19.4萬字5 12 -
完結129 章
惰性法則
你前男友有點礙眼。 容柯的頂流男友跟別人官宣了。 得知這個消息時,他正準備拒絕給他遞名片的男人。 掐了煙,又看了眼名片,是圈內最頂尖的時尚雜志。 容柯收下名片,語氣懶散隨意:“你想怎麼拍?” - 閆致一直以為容柯是個保守的人,沒想到拍攝當日,容柯比他想象中大膽許多。 他把這歸結為演員的職業素養,直到撞見容柯和男友分手,他才知道容柯的表現只是反常。 見容柯被一頓數落卻懶得反駁,閆致“好心”地上前幫腔:“你昨晚表現很棒。” ——指拍攝。 男友目瞪口呆地看著兩人,容柯知道閆致又是閑得沒事,也懶得澄清:“是你引導得好。” - 過慣了糊逼生活,容柯沒想到有朝一日會空降熱搜,甚至壓過了前男友的新劇宣發。 所有人都很好奇:這人是誰,閆致為什麼這麼捧他? - 閆致×容柯 王子病×懶散掛 - *攻很美很霸道,隨心所欲的時尚圈太子爺。 *受很帥很佛系,拍戲當作上班的過氣演員。現代|沙雕|甜寵|HE|雙男主|純愛|娛樂圈|爽文19.6萬字5 19
溫馨提示
加入尊享VIP小説,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,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
進入VIP站點

 上一页
上一页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