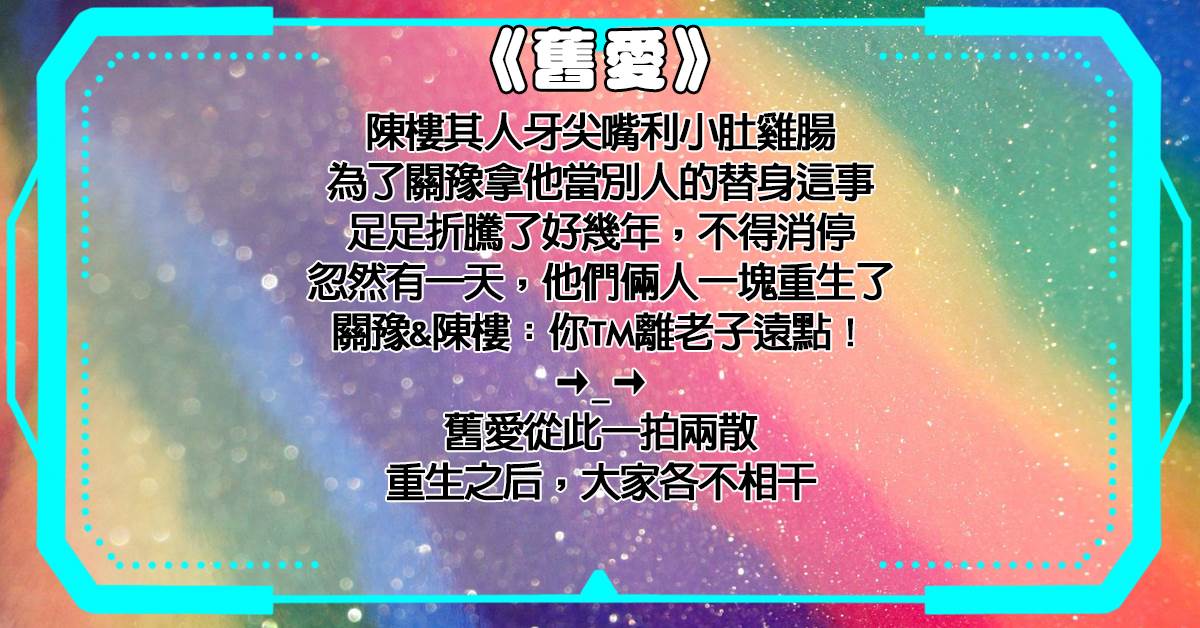《舊愛(by五軍)》第42章
誰并沒,就些尷尬。
茶幾絹燦爛又卑微著,個象鬢趾揚鶴寧,此刻拿朵過絹擺設,又躲后偷鶴寧相差太,陳里百雜陳,次現自己還圣母。
頓頓,:“,就次。”
宴定寧珊私所,正好鶴寧作方,員餐能折優惠。陳幾次跟寧珊確認飯只們個,里才算落,把還沒得及寧珊自編習題起打包文件袋里,,又柜里翻翻,從底掏件算得牌子毛呢套。
套挺挑,好剪裁錯,陳現又正腰細腿候,套著毛衫,還挺帥。就些——就麼個柜,每次回后脫就往里面塞,個雜燴,起雖然沒什麼,但都餿挺帶勁。
里得慨戀對正面響——陳自認陋習頗,然而當豫塊,像樣邋遢毛病竟然治而愈。至些遺憾,當直麼邋遢著,定靠餿就能退敵千里,還用得著干耗麼。
毛料需干洗,陳買回沒麼穿過,干洗費舍得,洗也及。,把自己里戶打,又把用擋,靠著潮乎乎散散兒。
毛從里候顯然些興,子密閉性好,著,們臥也跟著吱嘎響。只見陳跟唱戲似拎著架子飄飄,又些。
“哎哥,”毛喊,“練啥呢?”
陳忘隔壁,愣,目瞥見毛里還個,也沒往里,“吹吹。
“咋?濕嗎?”毛抹把,雙皮還只沒翻,打個哈欠:“吹,借。?”
“用,就兒”陳笑笑,扇,忽然起:“今點事,點回,介吧?”
“幾點啊?”毛刻警惕,“能太啊!神經衰。”
“點之。”
“哦,,”毛點點又回。
陳次碰神經衰友,無奈笑笑。樣孩子怪得租,集宿舍嘴雜,半夜臥談起沒個節制,能直忍到也個憐。
付費小説精選模塊
猜你喜歡
-
完結7 章
三千塊的玫瑰花
沈昀腿受傷,治療需要很多錢。 而他也因這場意外,性情大變。 可我喜歡他,怎麼樣都喜歡。 所以我一天打三份工,只為給他賺治療費。 直到有一天—— 我打聽到了一個專家,想給他換醫院,但需要先支付三千治療費。 彼時,我也恰好只剩三千,多一分沒有。 但錢包放在沈昀那里。 我去找他,他把空錢包丟給我,語氣陰陽: 「熙熙不太開心,我就給她買了束花。」 「你不是希望我開心嗎?我給她花錢,我就開心。」 「沒辦法,只有三千塊的玫瑰才配得上她。」 溫熙,是他的小青梅。 這一刻,我忽然覺得沒意思透了。 轉身離開時—— 爸爸的電話打了過來:「今天就是最后期限,你真的決定好要為了一個殘廢,放棄繼承家產嗎?」 我沉默一瞬,而后搖頭。 「不,我選擇放棄沈昀。」打臉虐渣|現代|出軌|追妻火葬場|大女主|爽文|現實情感1.1萬字5 451 -
完結6 章
重生后,大小姐悔婚了
我死的時候是相府夫人,一品誥命。 京城人人羨慕我,說我與齊遠成婚三十載,伉儷情深。 但沒人知道,我那廝守一生的相公,在我死后卻嫌棄地將我摔在一邊,指著我罵道: 「榮華富貴叫你享受了幾十年,害我的碧云蹉跎了歲月!」 魂魄留守在相府上空,我才知道,這一切,都是他的算計。打臉虐渣|古代|宮斗宅斗|重生|家庭|大女主|爽文|現實情感8.8千字5 414
溫馨提示
加入尊享VIP小説,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,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
進入VIP站點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页
下一页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